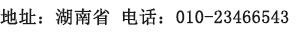段镇在讲课
在中国少先队历史上,段镇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和创造力的人物,也是集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之大成的少先队教育家。我自年起多次采访段镇,甚至在他家里居住半个多月,为其写成长篇传记《解放孩子》,于年出版。上海几代人都亲切地称呼他“段伯伯”,可谓男女老幼通用的爱称。30多年深度交往,段伯伯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:他把一颗心全部奉献给了儿童发展事业,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,是一个杰出的少先队教育家。
“迎接光明的新中国到来”
年2月,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批准段镇(当时名为段锦云)等入党。因为是地下的秘密活动,党员又是单线联系,每个党员的入党宣誓均分别举行。年7月,为16岁的段镇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,室外刚刚有一队日本巡逻兵经过。
在党组织培养下,段镇积极在青少年工人中发展党员,参加《新少年报》等各项工作,被称为一员“虎将”。对段镇来说,年4月3日地下少先队的成立,是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,因为他终于找到了为新中国贡献毕生力量的最佳事业。
一天,地下党支部书记胡德华约他谈了一次话:
“阿段,国民党叫我们共匪少先队,我们就成立少先队吧。组织上已经决定,由你负责建立地下少先队,团结广大少年儿童,迎接上海的解放!”
“您放心吧,我会完成党交给的任务!”段镇满怀信心地说:“可以用《青鸟》读书会为掩护,成立一个铁木儿团,稳健地发展地下少先队组织。”
胡德华满意地笑了,夸奖道:
“阿段成熟了,可以挑重担了呀。现在是秘密工作时期,不要公开用少先队的名义,要保护好每一个队员!”
经过地下党支部对各个《青鸟》读书小组的分析,决定分别在沪西、沪中、沪南、沪东、沪北等区的小通讯员中,秘密建立地下少先队组织。年4月4日,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儿童节。前一天4月3日,恰逢星期天,上海地下少先队首批18名队员,分别举行了宣誓仪式。
不久,在段镇细心安排下,沪中、沪南两区的地下少先队员聚在一个秘密地点,讨论怎样开展队的活动。
有个队员不解地说:“反动派都说《新少年报》是共产党的少年先锋队机关报,说我们是‘小共党’,为什么不能直接用少先队这个光荣的名称呢?”
“是啊!”“我们也这么想。”好几个队员都轻声嚷嚷起来,并紧紧围住了段大哥。
段镇笑眯眯地分析了当前的形势,说:
“不论这个组织用什么样的名称,少先队的红领巾早已飘扬在你们心中了。现在就是定名为少年先锋队,你们也不能戴上红领巾呀!重要的是,我们这个组织应该发扬战斗精神,配合大哥、大姐姐工作,迎接光明的新中国到来。”
说罢,他拿出了苏联作家盖达尔的小说《铁木儿团及其伙伴》,请大家边读边讨论起来。其实,这些队员已经熟悉铁木儿,但经段大哥一引导,他们一下子开窍了:“对呀!我们也可以像铁木儿那样做呀!”“铁木儿才是真正的少先队员呢,应当向他学习!”“我们也成立铁木儿团!”“要像铁木儿那样秘密行动!”……
兴奋起来的队员们献计献策,设计出了铁木儿团的统一标志:。“T”代表铁木儿,“△”代表广大少年儿童。这就是说,铁木儿团在少年儿童之中,要团结更多的小朋友来共同战斗;△也是五角星的一只角,五角星代表光明,象征中国共产党、人民解放军。铁木儿团是跟着中国共产党、人民解放军去迎接光明的。
段镇本是地下党委派做地下少先队组织发展与联系工作(即如今的辅导员工作),但在选举中,队员们一致推选段大哥为铁木儿团团长,推选地下少先队队长李森富为副团长。从此,段大哥既是他们的辅导员,又是他们的团长。
一个个地下少先队员就像一颗颗种子,在地下党培育之下,很快便在上海一些学校生根发芽了。
立文小学里的铁木儿“三人小组”走在最前面,一件事就使名震全校。段镇和原地下少先队员家振曾这样记述铁木儿团的行动:
一走进立文小学的校门,就闻到一股臭味,原来校门正对着厕所。学校想省钱,没有专职清洁工,一些同学又不注意公共卫生,抽水马桶坏了不修理,日久天长,越来越脏。厕所的板门因为太脏了,推门时大家不愿用手,都用脚踢,很快就把板门踢了一个大洞,阵阵臭气就从这破洞里扩散出来。
立文小学铁木儿团的三位团员悄悄地行动起来。一个星期天早上,三位团员瞒着家人来到学校,刚进校门就被传达室的老伯伯挡住。老伯伯怀疑地问:“今天不上课,你们来干什么?”三位团员支支吾吾地说不清,这更加重了老伯伯的疑心,他坚决不让他们进去,还说明天要报告校长,这一来可把他们难住了。三人退到隔壁一条弄堂的转角,立即召开“紧急会议”。他们记起大哥哥讲过争取群众支持开展各项工作的故事,想到传达室老伯伯是好人,应该争取他的支持。于是,他们重新又回到学校门口。
老伯伯看见他们去而复回,感到奇怪,反而要他们进传达室,想好好盘问一番。可这几个孩子不说别的,却问老伯伯:“老伯伯,这里怎么这样臭啊?”一句话引起了老伯伯的不满,他发起牢骚来了:“喏!就是那厕所呀,脏了没人刷洗,坏了没人修理,门也给踢破了,我最倒霉呀!一天忙到晚,看门、摇铃、搬东西、扫操场,让校长再用一个校工打扫厕所也不肯,真是……”
三位团员看到机会来了,马上接口说:“老伯伯,我们来打扫好吗?”“你们?”老伯伯像听到什么古怪的声音似的瞪眼望着他们。三位团员立即你一言,我一语,把他们要“尽力做看不见的好人好事”这一愿望告诉了老伯伯。说得老伯伯又感动又欣喜,高高兴兴地让他们进了校门。三个铁木儿拿出准备好的铁桶、石灰、抹布、木板和锯子、刷子等,投入紧张的战斗。在老伯伯配合下,抽水马桶修好了,用“来沙而”药水消了毒,洗刷得干干净净,还用石灰水把厕所粉刷一新,门也修好漆了一遍。
星期一清早,老师、同学们一进校门就发现厕所大变样,墙上还贴着一张“忠告”:“看,厕所现在多干净呀!臭气没有了,门也修好了。但是,一、请你保持清洁,用后放水冲洗;二、请你用手推门,不要用脚代劳;三、请你……”署名:“△T”。
△T是谁呀?全校同学都议论开了,反正,是做这件好事的好人呗!有人向传达室老伯伯打听,只见老伯伯直摇头:“不知道,不知道。”
铁木儿团的活动在勤光、位育、立文、储能等小学和建承、中法、市西、洋径、育才等中学里十分活跃。有的学校团员多,有的只有一二个,但他们都能按团章的要求认真去做。一时间这些学校里好人好事大量涌现。随着这种新风吹进学校,同学和老师的精神都为之一振。
△T在少年儿童的心中扎下了根,一批敬佩“铁木儿”行为的同学,千方百计寻找着铁木儿团。而铁木儿团呢,经过考察和讨论,把最积极的同学一个个地吸收到自己的组织里来,学校里的队伍不断地壮大起来。
本文作者孙云晓(左一)与段镇(左二)等合影
沉下去,“海底探宝”
年上海解放后,段镇担任团市委少年儿童工作委员会组织科长,他没有浮在机关忙忙碌碌,而是把大量时间用来去基层学校蹲点。
少先队建队50周年时,段镇回首往事,感慨万千,写了一篇谈蹲点的重要文章。他写道:
我从事少年儿童工作和少先队工作从“地下”到“地上”,从筹建中国少年儿童队直至今日少先队,前前后后总共有54个年头,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少先队,这是我的幸运。如今虽已年过七旬,仍能快乐地为少先队奋斗。我的座右铭是:“甘为红领巾孺子牛,誓当少先队敢死队。”我想我将干下去,干到死而后已。
我的领导,我的老师,那些大哥大姐们传授给我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,其中最珍贵的“宝贝”是群众观点、群众路线。它是少先队工作的“法宝”,又是培育锻炼少年儿童工作者的“法术”。建队50年来,我就是这个“法宝”、“法术”的学习者、使用者、体验者和受益者。
段镇在肇周路小学期间,与大队辅导员刘元璋一起,总结创造了著名的“友爱小队”经验,这完全是从队员的实践中来。
一天下午,段镇正和刘元璋在商量事情,副小队长张元元推门进来,急匆匆地说:
“辅导员,小队长陆幼珍两天没来上课了,怎么办?”
他说话的态度,既不焦急,也无同情之感。两个辅导员还未回答,他接着又说:
“准是逃学了。哼,还是小队长哩!”
“你推测她一定是逃学吗?”刘元璋重复地问了一句。
“一定是!队组织应该处分她。”
“现在我还不能同意你的意见,我不赞成随意批评一个人!”刘元璋说,“我看,还是按照中队辅导员的建议,先派一个同学,或者你自己亲自去一趟,了解了解她到底为什么不来上学,弄清楚了事情原因,再来决定是否要批评,好不好?”
张元元的脸骤然地红起来了,两手搓着衣角,也许他事先没有料到辅导员会这样回答吧。为了使这种不协调的空气快点散开,刘元璋扶着他的肩膀说:“张元元,我思考再三,最好还是由你自己去完成了解的任务,不知你是否愿意?”
“好,我现在就去!”张元元兴奋起来了,话刚说完,就飞也似地冲出了办公室。
第二天早晨,段镇和刘元璋吃过早餐,刚刚走进大队部,张元元就来了。紧接着,中队辅导员也匆匆赶来,她也是来谈陆幼珍缺课的事。
三个辅导员交换了一下眼色,示意张元元先讲。
张元元的表情和昨天下午来报告时的状态大不相同,脸上已经没有昨天那种毫无同情之感的神色,而是相当严肃地汇报说:
“报告辅导员,我已经到陆幼珍家去过了,她不是逃学。”
“那为什么不来上课,又不请假呢?”刘元璋急着问。
“她的弟弟病得很厉害,妈妈要去上班,又要请医生、买菜,只能把陆幼珍留在家里照顾弟弟,而且也一时抽不出身来请假。她见到我去了,很着急,说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病好,如果老不到校上课,功课会落后,她担心赶不上大家……”张元元愈说愈急促,看样子已动感情。他最后问:“辅导员,你们说该怎么办呢?”
“是的,怎么办呢?”三个辅导员都在想着这个问题,以至于忘了张元元站在一边正等待着他们的回答。
“我知道,昨天是错怪了她,随便说人家逃学。可是现在……”他自言自语地像在做检讨似地说。
这时,中队辅导员讲话了,她说:“我们大家应当立即想办法帮助陆幼珍。”
段镇和刘元璋当然很赞成中队辅导员的建议,因为这正是向孩子们进行友谊教育的好时机。
于是,张元元活跃起来了,他说:“我们想今天下午开个小队会,由我报告访问陆幼珍家的情况,然后请大家讨论帮助她的办法。”
“好!我们也来参加。”
出乎意料之外,这个平时并不怎样关心人的小队,在讨论帮助陆幼珍的问题时,竟是那样的一致。当张元元报告完毕时,孩子们都抢着发言,情绪十分热烈。
“我住在她家隔壁,到她家去很方便,让我去帮助她好了。”一个队员说。
“我和她平时很说得来,我去吧。”另一个说。
“让我去好啦,我能帮助她补课,还会帮助她做点家务事。”
小队会很快做出了决定:从当天开始,由功课好、住得最近的朱珊和林小娥负责去帮助陆幼珍。“我们一定很好地完成大家交给的任务。”朱珊和林小娥激动地说。荣誉感与责任感在她们身上涌现出来了。两个孩子没有辜负小队的委托,她们实现了自己在小队会上的诺言。为了正确清楚地给陆幼珍补上落下的功课,上课的时候,她们更加用心地听讲;每天下午放学以后总是准时地到陆幼珍家去履行任务;每天早晨又总是把陆幼珍做的作业按时交给老师批改,一天又一天,从不间断。
不久,团华东工委举行少年儿童队工作讲习会,段镇被派去做专题报告,专门介绍肇周路小学培养团结友爱集体的经验。这是段镇第一次做带有理论性的经验总结。
少先队需要“自动化”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注重实践经验和自下而上教育的段镇,居然被打成“右派”,加上文革的磨难,失去了30年珍贵的工作机会。年,被解放出来的段镇已经50周岁。但是,他的经验,他的才华,他的斗志,依然光彩夺目。于是,一时间,段镇成了许多单位争夺的“宝贝”。段镇毫不犹豫地选定了回团市委少年部,回到他魂牵梦绕的少先队!
当若干单位争调段镇之时,他已经在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蹲点几个月了。电影《闪光的彩球》就是在这里拍摄,电影里的大队辅导员就是以沈功玲为原型创作。
多年以后,沈功玲回忆:
段镇来蹲点说来就来,非常突然。在一个静静的楼台上,我开始向他汇报工作,也讲了我如何费尽心思设计队活动,又怎样到处请人,可他似乎感兴趣的不多。我渐渐悟出来了,惟一使他兴奋的是孩子的故事,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