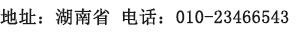我所亲历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(中)
金国范老先生于年参加 。在自始至尾3年多的战场生涯中,最令金国范老先生刻骨铭心的经历是年的第五次战役,迄今虽已超过70年之久,但其中一些细节犹历历在目,似如昨天。趁脑尚未锈蚀,如实地变成文字,与各位共享。当时作为新兵的金国范老先生,处于最基层位置,犹如森林中某棵树木上的一片叶子,无力解说整个战役的实际过程,只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、所见所闻,择其印象深刻者叙述于下。
生平首次讨饭
走啊走,突然在一交叉道口遇到了一支整齐的队伍,双人并排行走,武器齐全,原来是后撤的建制步兵。见我们这支由老弱病妇组成的队伍,根本等不及谦让,就匆匆把我们拦腰冲断。
孰知,我似仍在梦中只知跟着走,到天色微明,睁眼仔细一看,大吃一惊,我的那些哥哥姐姐到哪里去了?一问,才知我错跟着二十七军某师某团的战斗部队走了。
我赶紧转身往来路跑,行至交叉路口,咱们那帮人连影子都不见一个。我像只离队的孤雁,心中满溢着恐慌和无奈。四处除一些鸟鸣声外,连风也没了,显得格外静谧。天色逐渐暗淡下来,还飘起了蒙蒙细雨。怎么办?我停下思考了一阵:好像这条右转的小路是向东,如果加快步伐或许能追上那些老弱病妇。理清思绪后,我顿时来了精神,忘了疲惫和饥寒,追了上去。
近2小时追赶后,我肚子开始提出抗议。尽管昨天途中休息时,战友分了些干粮让我填了个半饱,但经历30小时连续行军之后,体内所储能量基本消耗殆尽。未挨到晌午,早已饥肠辘辘,全身乏力,眼冒金星。如灌铅似的双腿,拖着疲惫不堪的躯体,凭着惯性机械地前移。脑中冒出挥之不去的忧虑:还能坚持多久?会不会还没找到自家人就已晕倒在地,就此埋骨异国他乡?
忽然,我闻到一阵从远处飘来的米香,精神为之一振,不由自主地加快步伐往香味方向走去。只见不远处几块垒石上支着一敞口大行军锅,正冒着诱人的腾腾热气,两位穿着围裙的炊事员正不断地往灶肚里添柴。天助我也,若非云层遮蔽、细雨飘飘,谁敢白天生火冒烟?靠近一看,带着绿叶的米汤犹如茶水,白色的米粒在沸水中上下翻滚,真是粒粒可数。原来这是野战部队的一个连队,他们也几近断粮,偌大的锅中仅放了两碗米,余下的绿叶,则是从近处树上采来的桑叶。斯时此刻,饭香引得我控制不住口水外流。
于是,我厚着脸皮取出挎包内的搪瓷碗伸向锅边,愁眉苦脸不发一言,一副讨饭的可怜状。一年轻炊事员见此面露难色,婉言他们也饿了许久,这锅汤是全连四五十人今天的口粮。另一位满面胡茬的年长者见我好像连说话的力气也没了,问道:“小同志,你是哪个部队的呀?怎么只剩孤单一人呢?”我如实相告。他叹了口气说:“听你口音好像是南方人,小小年纪就离家到外国打仗,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真不容易啊!这样吧,就把我那碗让给你好了。”在我充满感激的目光和慌张不迭的连声道谢中,他接过碗,从锅底捞起碗“浓”汤,递到我手里。此时,那位年轻的炊事员,也默默地露出赞同的眼光。
这是我有生以来 次,也是至今 一次要饭经历。正是这碗以前从未尝过的、这辈子再也吃
不到的桑叶粥汤,救了自己的命。它赋予我力量,大难不死,路在前方!这碗充满战友情谊的粥汤,其味无尽,刻骨铭心,永生难忘!
路遇张尚武
喝罢米汤,再三拜谢后我仍回原路向东。约一个多时辰,见路边一人似战友张尚武正依树而坐。我入伍后不久,因希望学习医务知识和技能,从院部医保股下放到一线医疗队与张尚武同一医务班。他来自皖北农村,尽管只有小学文化,但已干了好几年医务工作,见多识广有一定经验。老张为人憨厚老实,待人和气,我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一年多,他平时对年幼的我挺关照,我们两人关系不错。他身体差,是个心脏病患者——二尖瓣关闭不全。
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,部队刚进城不久,医院的医疗技术水平低,遇见此类心脏器质性病员,没有条件手术,只得做保守性治疗。军医查完房回休息室不忙时,会让老张脱衣招呼大家用听诊器听他心跳发出的噗嗤噗嗤杂音,再与正常人做比较,以提高大家对心脏病的认知。平时老张工作兢兢业业、细致认真,对伤病员态度和蔼,深得一致好评。记得昨日他心脏不适,由同伴们扶着慢慢前行,此时怎么会在这里独自一人呢?
趋近细看,果然是老张,闭目冥坐似睡非睡。我靠他耳边叫了声,他才慢慢睁开眼睛,有气无力地从牙缝里挤出一点声音“:啊,小金!”原来,经过连续三四十个小时奔波,没吃没睡,他心脏难受得无法忍耐,实在迈不动步了。他接着说:“我自己提出让其他人先走,这样他们或许还能有生路。你怎么也一个人才到?”看他哆哆嗦嗦开口困难的痛苦状,我将与他别后一天多的经历简单诉说了一番。
正谈着,过来一些掉队战士,我马上前去求救。听我说明情况后,其中一人给了我俩干粮各一小块;另一位见我们手无寸铁,则从子弹带中抽出个木柄手榴弹,递给老张并交代“:这可用于不愿做俘虏时。”我趁机与他们核对自己的行走线路,证实方向基本正确。老张 用力挤出几句话:“你别管我,跟他们走,也许能赶上我们的人。跟着他们是条活路,否则只有死路一条。”我俩对视瞬间,他的泪珠夺眶而出。我转头不忍,思考片刻,终于接受了他的忠告,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。
老张直至战役结束都没归队。停战后通过联合国机构,讯问是否有张尚武被俘或庾死战俘集中营的消息都无下文。由此推测, 可能是饥寒交迫而发病,客死异国他乡。
夜宿山间小屋
跟着这支队伍,我感觉有了依靠,情绪比孤单一人要好得多。虽然尚不清敌情,但他们说,我们现在大概已过杨口,往东是麟蹄,向北可去金刚山或淮阳。 避开麟蹄,据说那里北进的是李承晚部队,尽管战斗力和装备不如美军,但目前我们缺乏弹药口粮,真遭遇了也不易对付。不过其中有两名战士因其部队预定赴麟蹄,故分手告别朝东归队,余者则选择往北。
天又暗下来,雨比刚才猛了,路更泥泞易滑,大家急于寻找避雨之地,但无处可躲。领头者转过一个山头后高声大喊,快过来,这里有间小屋。大家心情为之一振,加快步伐,向那里走去。走近一看,估计是守林人休息用的茅草房,大间可供住宿,小间堆放杂物,门窗皆无,室内空空如也,仅有一具穿着韩国军装的尸体,双目紧闭仰卧在地。众人围着看,其肩章一条杠一颗星,应是个少尉军官,不知何因陈尸于此。死者脸色苍白但英俊,且衣着整齐。我们中的一位胆子较大者,顺手掀开其上衣一看,见他腰上皮带光亮无损,就动手欲取下做战利品。孰知,解开一抽,发现一股尚未完全凝固、暗红色的带脓液体从伤口流出,一股腐臭气随之扑鼻,同时冒出不少蝇蛆。围观众人皆捂鼻转身,令他急忙住手。
此时,我甚感口干饥饿,在储藏室一隅,找个可以依靠的墙角,放下背包坐好,将与老张分手前好心人给的、舍不得食用的应急干粮,和水一起细嚼慢咽徐徐吞下。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走,不时会遇见溪流,一旦壶中缺水,即加以补充。当然,都是生水,即使稍有些浑浊,但也顾不得许多。好在经过天然过滤净化,无细菌等有害物,至少这几天我肠胃没出问题。疲惫至极的我困意袭来,勉强嚼完,头一歪就进入梦乡。这一觉不知睡了多长时间,醒来发现已是深更半夜,黑暗中除死人和自己外,已无他人。禁不住喊了声:“有人吗?”没有应答。心中有些慌,定下一想,既然如此,那死者不会复活,且自己与他不在一屋,还是安心等天亮再说。
虽然这些同伴没叫醒、带我一起上路,心有所怨,但又想,或许人家叫了,我太困不醒,见我实在太累而放弃。事已如此,何况孤身一人已非初次,只要走得动,一定设法归队。只有回到那些朝夕相处,一起吃饭、睡觉、工作、学习、交心、患难、生死与共一年多的集体——我们的医院,自己的心身灵魂才能得到安宁。没饿死,还有力气走得动,就有希望!
走过双木桥
一坐下去,瞌睡又来,似睡非睡地时间就过去了。等清醒天色已明,但空中仍云层密布,我赶紧起身找回来时的小路,继续冒着逐渐变小的雨势前进。陆续又遇到一些步兵,仍是九兵团的。爬过一个不算太高的山头后,谷地似乎开阔起来,我比不上那些体能好的人,又落单了,只身沿着一条溪边小径,往前溯流而行,以期找到较窄处越过。
眼见溪对面人较多,还有骡马,故急于想过溪与其会合。此溪平时大概仅两三米宽且不太深,但连日阴雨,涨水变成五六米宽,难以逾越。那时我还不会游泳,如果水达胸部人会站立不稳,水流再达一定速度就会被冲倒。喝几口水或许能过去,但背包必然落水,弄不好会被淹死。我边走边观察,见一较窄处水清澈可见底部卵石累累。经一番思想斗争,我决定冒险趟过去,当即将背包顶在头上,以防被水浸湿,并将鞋、袜、裤脱下捆好仅剩短裤,用光脚试探了水温,确实很凉,但咬牙尚能忍受。没走两步水已至膝,第三步差点湿了短裤。这个位置离最深处还不到一半。
这时,一穿军装中国人见我涉水叫道“:太危险啦!快穿好衣服,顺着溪向前,没多远有座独木桥。”我一听,大喜过望,忙不迭转过身来,不及细看,一脚踩在块活动的卵石上,身子一歪,忙着护背包,却把整条短裤都弄湿了。上岸见无他人,我光腚直接套上长裤,把湿透的衬裤拧干,放在裹有雨披的背包上拴着晾晒,以防丢失。走了约刻把钟,果然看到由两根不粗松木组成的双木桥,木头两端断面还留着被斧头砍凿的新痕,比真正的独木桥要好走且安全,没几步就跨了过去。回想刚才的情景,总算有惊无险,也下定决心今后定要学会游泳。
此时雨虽已停,空中云层仍较厚。突然远处传来飞机的马达声,却不知飞机在何处。突然一阵阵娇滴滴的比马达还响的声音,从空中而至“:共军官兵们注意,你们已经被联合国军包围了, 的出路是放下武器,举起手来向我们投降。我们一定按照联合国规定,保证你们的安全,让你们吃饱,有伤、病会得到救治,有地方休息……”听此声音在头顶上反复广播,有人就骂了起来。突然,边上有人端起长枪,朝天放了一枪,倒把周围的人吓了一跳。马上传来一个声音:广播的是录音,不是真人,甭浪费子弹。众人哈哈大笑起来。趁着气氛不错,我小声问旁边的人,我们现在仍在敌人包围圈里吗?看见过美国兵吗?他说“:不清楚,但至少还没面对过联合国军,只见过南朝鲜兵。”
未完待续
编辑:黄云煜皓
审核:周文轩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